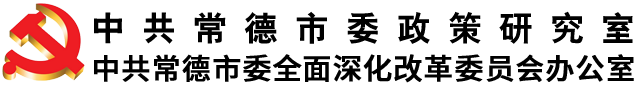读书治学“很好玩”——遥想民国学人的风趣风雅与风骨
彭 镜
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一句“雪夜闭门读禁书,不亦快哉!”不知激发了多少读书人对此种读书意境的想象与躬行。其实抛开读的是否为“禁书”不论,单就“雪夜闭门”,就足以让人心生惬意的了。国学大师林语堂将金氏之意境又作了进一步发挥,在《读书的艺术》一文中,他描述的场景情调简直妙不可言,“在一个雪夜,坐在炉前,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,身边放一盒淡巴菰(雪茄烟),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,经济学,诗歌,传记的书,堆在长椅上,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,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,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。”自小被称为读书种子的林语堂,最是推崇闲适、快乐读书。在他眼里,若感读书是门苦活,则不如不读,悬梁刺股那样炼狱般的读书生活,林大师可能从未尝过。
1939年秋,文学巨擘钱钟书与友人从上海动身,同赴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,途中一月,钱钟书整日手捧一本《英文字典》读得津津有味,旁人不解,问其缘由,他则随口一答“很好玩”。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,能说33种汉语方言,且精通多国语言,他曾告诉女儿,自己研究语言学就是为了“好玩儿”。这就很值得玩味了。象王世襄玩遛鸟、李叔同玩字画、黄永玉玩收藏……人们好理解,这本身就是在“玩”,都是些闲情雅致的艺术活动。但对钱钟书、赵元任之“玩”则大多感到不可思议。其实在民国时代,象钱赵两位先生那样感到读书治学“很好玩”,却是不少学人的真实学术态度,也是在战火纷飞的民国时代何以学术大师辈出的关键密码。
因为在民国学人们看来,读书治学之于人若很大程度是,甚或仅仅是谋取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梯子,“苦”就是自然的了。宋真宗赵恒在位期间(997—1022年)治绩平平,但却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《励学篇》,里面充斥着劝人求取功名利禄的形象比喻,原文如下: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;安居不用架高楼,书中自有黄金屋;娶妻莫恨无良媒,书中自有颜如玉;出门莫恨无人随,书中车马多如簇;男儿欲遂平生志,五经勤向窗前读。在取得功名前的漫长读书生涯,则基本可用“苦”字来形容,什么“十年寒窗无人问”,什么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,什么“吟安一个字、捻断数根须”,什么“衣带渐宽终不悔、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以至于还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……顺着大宋皇帝指引的路径,极少数读书人经“苦学”如愿以偿获取了官位、财富、美人,而绝大多数则活到老、念到老、考到老,屡考屡败而又心有不甘,不少学子最终沦为鲁迅笔下强辩“窃书不为偷”的孔乙己。
当然,这笔账也不能全记到科举制度上。历史上科举制也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选择机制、一种必然存在;更不可“一篙子打翻一船人”,将皇权社会的读书人就看成铁板一块。要知道,尽管身处“万般皆下品、唯有读书高”的功利社会,有“朝为田舍郎、暮登天子堂”的美好愿景刺激,但早早就厌烦求取功名之路,抛却悬梁刺骨之痛,向内发掘本心之需,自觉追求读书之乐,通过读书怡性情、养大德、求真知的也大有人在。这种人,可算是真正解脱了、放下了、活明白了;到这时,读书也就真正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“一种生活方式,一个平生最大的爱好”,成为一种值得孜孜以求、沉醉其中的至乐之境。金圣叹能说出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之妙境,根本原因在于他尽管“应科试、考第一,但绝意仕进,以读书著述为乐”。换作权欲利欲熏心的“苦读”之辈,就算屋外飞雪漫漫,手捧踏破铁鞋都难觅的“禁书”,也是难有畅读之情趣的。
民国新文化运动可比西方文艺复兴,如恩格斯所言“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”。爬梳民国著名学人的读书治学生活,从中的确可以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,也可说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,即:真正的大师级人物,往往出自“玩学问”的那批学人。他们至真至纯、志存高远,视自己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、传薪者,读书治学的终极目的,就是要在西学东渐、中西文化交流交锋的时代,推动中华传统文化(特别是儒学)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,重登世界民族文化的高峰;他们也自得其乐、乐在其中,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锱铢积累而又乐此不疲。围绕着做学问,出了一批好玩的人,也生出许多好玩的事,读来令人捧腹而又心生温情和敬意。在民国学者眼里,学问,一可作资本炫耀。比如声称50岁前不著书的经学家黄侃,对前来问学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就颇不耐烦,“小学(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)是很难的,你还是去弄你的经济学吧!”又说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有个习惯,在课堂上讲到要紧的地方就停下来了,然后对学生们说:“这里有个秘密,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,还不足以让我讲,你们要听我讲,得另外请我吃饭。”这样的轶闻趣事,在民国学人传记中有大量记载,其中尤以余世存的《非常道》描述最为传神。学问,也可比终生伴侣。像 “清华三孙”(叶企孙、陈岱孙、金岳霖)那样学问好、名气大而又终生未婚的民国学者还有不少,就是结了婚的,也时不时讲出一些对学术职业格外动情的话,哲学家贺麟就公开说:“可与妻子离婚,但与哲学离婚做不到。”学问,更可为成全自我、实现价值的志业。在民国,辞掉官职、脱下军装而回归书斋的学者不在少数,如熊十力、刘师培、刘文典……,这是一长串名字。使命感也罢,真性情也罢,在他们的内心深处,终究认为做学问有趣些、好玩些。比较而言,民国时期那些皓首穷经、苦心孤诣的学者,却往往出不了大学问,其迂腐天真的学术观点及行事风格,多年后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。
《冰点周刊》主编徐百柯就认为,“在今人看来,淡淡一句‘好玩儿’,背后藏着颇多深意。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,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。‘好玩者’,不是功利主义,不是沽名钓誉,更不是哗众取宠,不是一本万利。”诚哉斯言!今天我们读书也好,治学也罢,还真得象民国学人那样,要有股“玩”的风趣、风雅、风骨注入其中,如琢如磨,如痴如醉,方抵妙境,方能精进,方有所成……